相遇是一場想像力的遊戲:敞開幽微之境的「空氣草」|文:邱筱臻
多樣性媒介浸染著我們的日常,數據匯流成生命各種不可或缺,展覽所形構的世界正如平行於真實世界的時空,一如網絡空間,在此,藝術家成為某種形式的程式設計師,在符號和意義之間創造路徑或場景;藝術作品不再是創作完成結果,而是成為鏈結時刻的無限迭代(Iterative Method);而觀者可在此現身,依隨展覽文本或作品本身,以多種感官介入去創造各自的解讀或成為某種程度的共同創作者。在此情境下,我們該以何種角度來看待「空氣草」所欲帶給我們的訊息與啟示?
遇見「空氣草」−策展敘事的想像
十九世紀,英國華德博士(Nathaniel Ward)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發現生長於密閉玻璃容器內的植物,即使沒有大量的土壤,也沒有尋常的澆水灌溉,卻能自行形成循環體系,並且在其中進行光合作用,開展出微型生態,這就是對於保存、運輸植物具重要作用的華德箱(Wardian case)。華德箱,只是一個玻璃瓶箱,卻在當時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植物獵人羅伯・福鈞(Robert Fortune)依靠它將安徽與武夷山的茶樹種子與幼苗移植到當時的印度喜馬拉雅山區,影響了茶葉生產的格局;克萊門特・馬克漢(Clements Markham)亦藉此從南美將可提煉奎寧的金雞納樹運往英國和加爾各答,解決飽受瘧疾肆虐之疾苦……看似微不足道的玻璃瓶箱,卻在此處到彼方轉移中,一點一點地改變了整個世界。
「空氣草」展覽,一如華德箱,創造了蘊含生機的環境,悅納異質多元的作品,打開格式之外的疆域,在此,生命生出生命,自成一生態宇宙,迎向尚未成形的未來。「空氣草」的指涉則來自策展人張君懿從同名鳳梨科植物所得到靈感,以其生命形象比喻「自由活躍的藝術創作主體」,更以尼可拉.布希歐(Nicolas Bourriaud)的「莖上根(radicant)」象徵無所不可著生的狀態,可探索他方、理解他者;以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地下莖(rhizome)」如遊牧般多樣化拓展的過程,形成無限延展的開放思維與可能性。意圖讓展覽成為「一畝富孕育力的藝術實踐田野」,開發一個創作的空間和視野,提供另一種看待藝術的方式與態度。
藝術家從事藝術創作與個人脈絡和社會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一方面,藝術家的知識與信仰影響了他對社會的觀察和人生體驗;另一方面,藝術家的創作也與其生活時代、經歷和實踐密不可分。「空氣草」並不致力於瓦解個人主體性,而是提出一種可逃逸於既有框架或慣性思維的可能,和藝術家們協力在目前的世界鑿開一道穴口,以反思所承繼的一切、以召喚地穴之外關於藝術創作的想像。這樣的策展角度使藝術家們可「走出經久固著的原生地,與自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保持距離」。也正是透過這樣的思想距離而使創作主體在自我檢視與對藝術現象的觀察中,「瞥見那些駐留在思想已久卻從未察覺的事物」,並「察覺同時作為條件與界限的創作思維本身」。因此,不再只以跨域限縮視覺和表演的交流與互滲,而更強調在藝術創作不斷向外擴張的傾向中遍歷域內與域外,在彼此相遇主體化的整體重構中實現了當代藝術特有的美學動力。一如「空氣草」論述:「在與他者對話或從環境汲取養分的過程中,開展出更具創造力的個體」。
「空氣草」表現出對藝術展演力的信心,但並不刻意安排某個主題或某種形式,而是聚合創作主體穿越各自的現實經驗,在這過程中涵納不同思想脈絡與創作曲線,進而撩動某種關於藝術展演的想像。或許,正如波赫士所言:「採用笨拙的隱喻,明顯的迂迴,也許是挑明謎語的最好辦法。」空氣草的形象並未在作品中現身,但空氣草的意象卻因此在展覽中永遠在場。我們可以意識到,一個展覽無法只滿足於服膺藝術史脈絡或追尋議題式論述,而開始回歸思索藝術創作主體,試圖在彼此相遇、我者的轉化與他者的流變中,激起新的思考邏輯與敘事型態,甚而探索未知的表現模式。
是誰遇見誰?−「空氣草」的現場想像
在此涵構之下,「空氣草」成為一個相遇的場域,布希歐曾說,藝術是相遇的狀態(état de rencontre),因此而有了交流的時空觀,作品不再是一個穿行閱覽的空間(espace à parcourir),而是一個體驗感知的時延(durée à éprouver)。也就是說,作品或展覽不再是一個客體的生產,而是一個交流對話的創造。「空氣草」座落於兩個不同的相遇場域,一個空間曲褶繚繞宛如迷宮,一個動線澄明卻寓意繁複,兩種不同質地的展覽場域建構出「空氣草」多元景深的時空感,而這多維景觀性結構來自於藝術家介入空間的書寫,建構出一個既真實又夢幻的瞬間,以及觀者參與作品的對話,創造出某個發展關係的時刻。
−關於「現場(in situ)」的感知流變
假如一個地域必有一段記憶、一種風景,必然存在某些共通點,可能是人、物體、事件以及場景;但即使在同一片土地,每個人仍有其特有之記憶與風景、一些對個人而言獨特的卻對他人而言可忽略的細節。藝術家的介入成為召喚場域意識的觸媒,他們捕捉空間中所遺留的痕跡,挖掘其隱蔽的精神面向,建構有關或無關當地記憶的獨特敘事;而作品產生的連結或斷裂則邀請觀者漫步其間,以自己的身體感知和社會經驗探尋相異的視點,進而參與創建全新的關係。


北區藝術聚落,舊眷舍的遺留痕跡勾勒往日輪廓,彷彿還能窺見迴盪於空間中的生活故事,展場的當下與空間的過往雙重時空並置;而順著街道蜿蜒於巷弄間,似近還遠的人聲車聲又使得現時的生活場景與當下的展覽場域重合,形構成三重時空交錯;眼前分岔的幽徑,帶著觀者持續穿梭於虛中帶實、實中帶虛的歷史軌跡與故事現場。當藝術家來到這個社區,進入老舊屋舍,與其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產生對話,即是相遇之始;當觀者走進展場,周遊於作品,與其現場發生某種情感關聯,即是關係生發之始。


蔡影澂的《No. 212》利用社區植物造景層層堆疊,繪畫於瓷磚上的葉片、漂浮於水面的落葉和天光雲影的草木樹石,各種層次交錯烘托出立體景觀,描繪某個徘徊庭院池畔的瞬間,是水池如時空膠囊般植入瓷磚這記憶載體的層疊時空;何采柔與黃思農的《254円》以文件、物件和影像建構敘事的可能,透過遺留物尋找湮沒於塵囂中的無名者,重現過程虛構曾(或不曾)存在的記憶,觀看的角度形構虛實相合的事件巢城,引發期待懸疑揭發的張力,在此處與當下被觀看主體感知與參與,而生成不同的意義與想像,現實和記憶轉換皺褶出跨時空的現場感。
倘若克里斯多・耶拉瑟夫(Christo Jaracheff)和珍娜・克勞德(Jeanne Claude)夫妻以包裹方式試圖喚起觀者探索表象覆蓋下的真正面貌,郭月女的《層狀空間》則從皮層意識與身體感知出發,將建築物的內外與身體的表裡互文,透過樹脂等材質,脫落身體的表面層次,架構建物的內在層次,佈置出牽引觀眾感知的另類空間;而大觀路旁李蕢至的《回收風景》,枝幹蔓延錯綜著現實與想像,泥沙痕跡堆疊著地景與記憶,樹根攀爬纏繞彷彿破牆與屋中之樹相連……以當地素材重建的往日情景,在光影與氣味的渲染下,帶領觀者進入時空夾層,回到了某個氾濫淹水的當下,又或者呈現某種被隱藏的地景,反映了這特殊環境真實與虛構交錯的場景。
徐瑞謙以不同材質的物質與軌跡形成暫止空間的《從》,則是具有強烈空間存在意識的現場,看似寂然不動又恍如轉眼便將流動的物體,猝然頓挫凝結出材質運動的張力,各式各樣的相互對話與動力關係潛藏在事物與空間本質之中,當觀者進入,不只是來到雕塑之域,更來到物質遊戲後的空間;盧詩潔的《表演者》和《2017指令?舞蹈?》則透過一大片的藍抹除了印記繁複的眷舍空間,彷彿打開一道普通的門卻通向另一個世界,藍色基調與身體肌理透過數位的演算織構而成虛擬舞台,觀者在此亦可成為表演者,形構空間與感知的虛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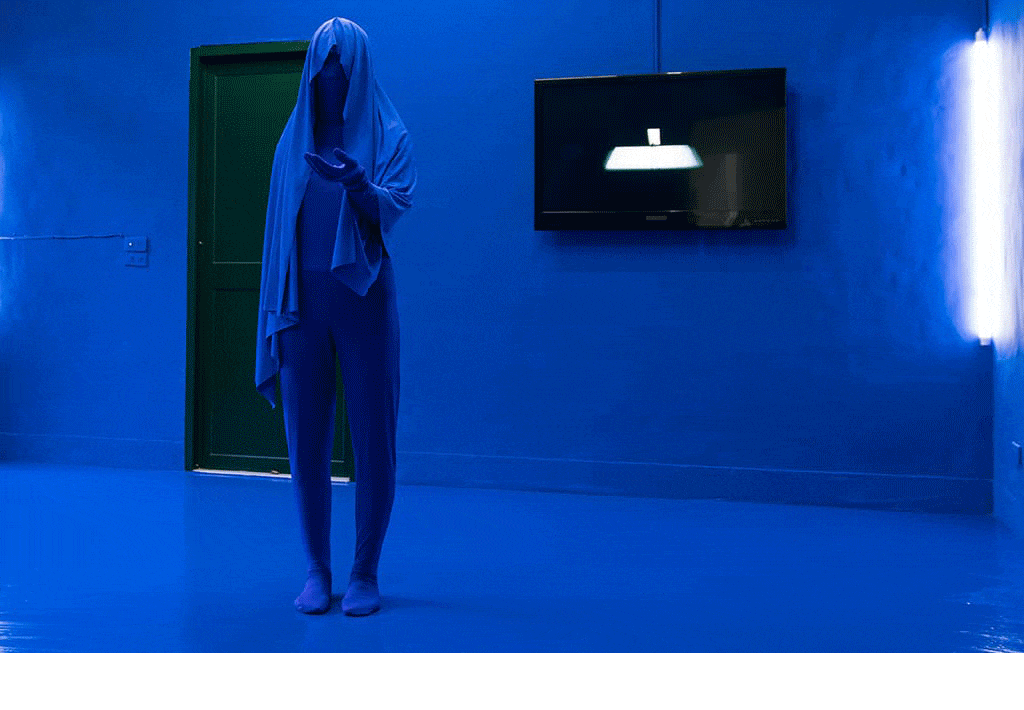 蘊涵人文性的現場展現在藝術家現身的場域,打破或倒轉「藝術家/人」的形式界域,觀眾的主體個性也在此呼之欲出。劉彥宏的《琉璃草——地水火風空界》從庭園到房間,以繪畫和物件佈置出一個近於日常的空間,說夢者與畫夢者以舒緩的步調在此聽夢、畫夢,以「慢」的移動和感知模式,創造一個讓觀者跳脫尋常時間邏輯的空間;縫縫工作室的《縫縫屋》,以人的表演介入空間製造情節,縫隙與縫補就像感性與理性的相互依存,觀眾來此注視縫縫的過程,注視空間的活化,和表演者一起以身體感探索空間的另一個層次。
蘊涵人文性的現場展現在藝術家現身的場域,打破或倒轉「藝術家/人」的形式界域,觀眾的主體個性也在此呼之欲出。劉彥宏的《琉璃草——地水火風空界》從庭園到房間,以繪畫和物件佈置出一個近於日常的空間,說夢者與畫夢者以舒緩的步調在此聽夢、畫夢,以「慢」的移動和感知模式,創造一個讓觀者跳脫尋常時間邏輯的空間;縫縫工作室的《縫縫屋》,以人的表演介入空間製造情節,縫隙與縫補就像感性與理性的相互依存,觀眾來此注視縫縫的過程,注視空間的活化,和表演者一起以身體感探索空間的另一個層次。
作品重構空間列序,生成藝術聚落生態的某種當代意識現場,這樣的空間質變出現在多位藝術家於同一場域構築獨立且彼此對話的作品:澎葉生(Yannick Dauby)的《軌跡與碰撞》在空蕩的屋舍中提供四種聲音的組態,音軌是他方的想像,聆聽卻是此處的感知,構成身體與聲音相遇的當下,一如Samuel Butler所言的既是「不在何地(no-where)」亦是「此時此地(now-here)」的時空感知;蘇威嘉的《自由步——聽身變位》,舞者身體細節以緩慢至凝結的影像形構舞動肢體的線條、造型、律動、音樂及光線,身體在此脫離生存的有機體,跳脫文化產物,回到身體本身書寫其無盡延展的空間,也使觀者從聆聽空間中轉向身體風景的凝視;而徐瑞謙的《從》也在此現身,物質媒材與音響裝置彼此延展共構場景,三件作品各自獨立,卻又以場域環境、建築肌理與觀眾參與,使影像、聲響、雕塑和舞蹈形成了一條動態路徑,牽引彼此微妙關聯。
「空氣草」就如一個微型生態的隱喻,在這裡「物質的每個部分都可以被構思成一座植物繁茂的花園,一個滿覆游魚的池塘。」然而每個藝術家的創作卻又各自獨立,一個作品或一個屋舍就是一個微微生態,觀者的介入也形成微微生態,「植物的每個枝椏,動物的每個肢體,它們的每一滴汁液又都是這樣一個花園或這樣一個池塘。」即使作品彼此之間未必存在必要性的關聯,同時展演於此時此刻的作品卻若有還無地處於共生狀態,甚至擴散而及北區藝術聚落周圍場域,「雖然花園中植物與植物之間的泥土和空氣,池塘中游魚與游魚之間的池水既非植物亦非魚,它們卻包含著植物和魚,不過極為細微而使我們難以覺察。」
−空間重構之想像物語
如果北區藝術聚落是藉著場域印痕並透過藝術家介入的書寫形構空間現場,有章藝術博物館則是場域的碎形與重組,白盒子與黑盒子重疊出具有情境感的空間。而這個鑲嵌於博物館的劇場空間,物質成為最主要的表演者與敘事者,真實的演出者(人)則化身為重要媒介,如油畫中的調和劑(painting medium),在藝術家的調度中,使動態或靜態的匯集展演成流動的時空。
在這流動的空間,差異與重複置入纖細的時間質感,何采柔的《等它飄到我面前,我會想起》以三個極其相似卻細微變化的房間,表現出等待的記憶落差。時間的軌跡隱藏在細節中,觀者的探索無法還原「等待」這個故事真相,反而在微妙的分別中構成記憶的虛擬性與多樣性,宋孟璇的表演介入更加深記憶的失衡感,在具疏離感的演出中,身陷時空失重的扭曲中。與何采柔作品相鄰而以某種形式對話的張永達《相對感度N°4−C》是流動載體銘刻時間的雕塑,三個厚鐵板搭配三種不同濃度的硫酸銅,間歇性的滴落交織而成時間風景。物件(鐵板、硫酸銅液)、行為(滴落)的重複與差異交互涵攝,形構一種細膩的時間感知,觀者可運用各自身體感官看見、聽見、聞到或感受到時間的流變。林人中的《有章藝術博物館行政專員的一天》是時空並置的日常展示與影像情境,博物館的展演時空與日常辦公時空錯置或挪移,影像是真實折射而成的虛構,館員的在場成為某種虛擬實境,現實與幻境彷彿一線之隔,觀者也許進入當下的真實時空,也許去向某個與真實近似的時空,就像村上春樹有兩個月亮的1Q84。
流動的空間亦開展為「自我」的複雜疊層,河床劇團的《我在沉睡的獅群中赤裸裸地站在街上》,以「鹿」的三種形象組構而成,繪畫裡的鹿頭凝視著你,手上卻舉槍執行著某種暴力行為;粉色舞台擺置著鹿頭標本,景框內微微的動搖晃出幻想與殘酷交錯的場景,景框之外回應的是觀者的自我折射;而一旁懸掛的獸骨,是一個生命瓦解之後的可能景觀;演出者的在場勾勒夢中鏡像,而觀者以其各自特異的生命經驗穿越時空迷霧,直視自我生命風景。
拉・里博(La Ribot)的《當心遭人模仿!》以暗室氛圍與羅伊・富勒(Loie Fuller)作品展開微妙對話。影像中有兩個身體,一個是彈鋼琴的卡爾斯・桑托斯(Carles Santos),一個是隱藏於手持攝影機後的拉・里博;前者是有形的可見,以身體主宰鋼琴的律動與音聲,後者是幾乎不可見的精神投影,透過攝影機將自我投射於影像與聲音中,觀者在黑暗中彷彿穿透柏拉圖的洞穴,進入另一個時空,而「我」在可見與不可見的臨界點上。克里斯汀・赫佐(Christian Rizzo)的《有些事正在進行……》以兼具劇場性與造型性的虛構想像探索示現與消逝;表演的影像片段或大或小地投射於黑暗邊際,物件或舞動或靜止地部署在空間,煙霧繚繞著真實與幻境,聲響跳接著舞台與展場,正是藝術家的前世今生;而觀者穿行其間,既走上了虛構舞台,也走進了藝術家的意識國度。
物件、聲響、影像、空間交織而成的複合體,疊置於細緻的時間性中,在動靜之間,觀者繞行其中,觀看、聆聽、感覺,以身體感知漫遊探索作品內蘊,打開彼此對話的可能。「空氣草」正是這樣重新注視藝術創作本體的過程,注視創作者的創造能量與自我思辨,也注視著觀眾的參與和感知覺醒。
「空氣草」,想像的持續綿延
電影「星際效應(Interstellar)」中主角在遙遠的太空跌入了多度空間而穿越時空,來到過去時間的夾層,試圖向幼時的女兒傳遞訊息。在弦理論(String theory)成立的狀態下,粒子的波動性質可讓維度組態互相跳轉,也就是說,時空的裂縫存在於空間的每一個角落,要脫離我們當下生活的宇宙,需要我們有足夠的能量鑿開蟲洞,使黑洞與相對應的白洞連結,便可穿越時空。正是這所謂的鑿開之力,使藝術實踐真正打開其可能性,而「空氣草」就如這鑿開之力,為我們打開了一個關於展演跟藝術創作的想像,繼而開啟藝術活動的新可能,切向另一個未明空間。
然而,「空氣草」並未嘗試透過展覽為某種新藝術活動「代言」,「空氣草」展示給我們的是藝術創作主體所形成的微型宇宙:每一位藝術家都有各自的形式領域、問題意識和創作軌跡,但並沒有以任何風格、主題或者圖像符號將之聯繫串連,而是在此呈展各自的理念與思維,共生為一展演生態體系。換言之,「空氣草」更著重於彰顯我者與他者流變的狀態,向外域擴展的思辨中回歸內域自省的狀態,並進而促使我們思考,在當今創作語境下,當代藝術展演的可能性。
顧城說:「藝術是花的時候,結出神的果,這時哲學是葉子。」一個展覽會萌什麼芽?展什麼葉?開什麼花?結什麼果?空氣草不說話,只在舒風輕拂中葳蕤綻放……。
———-
註1.莎拉.羅斯(Sarah Rose),《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 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呂奕欣譯,台北,麥田出版社,2014。
註2.張君懿,〈「空氣草——當代藝術中的展演力」策展論述〉,2017。
註3.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小徑分岔的花園〉,in《波赫士全集 I》,王永年等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p. 637。
註4.Nicolas Bourriaud, Esthétique relationnelle, Dijon, Les Presses du Réel, 2001, p. 15.
註5.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91, p. 96.
註6.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La monadologie, Paris, Vve E. Belin et fils, 1886, pp. 80-81. 【En ligne】BNF Gallica http://gallica.bnf.fr/









